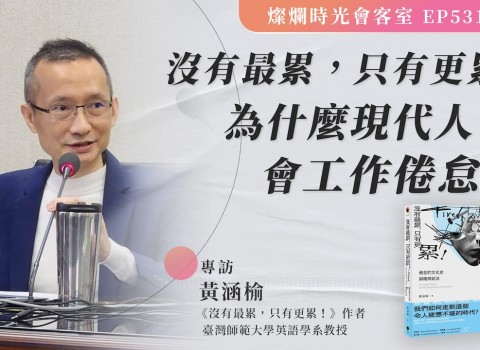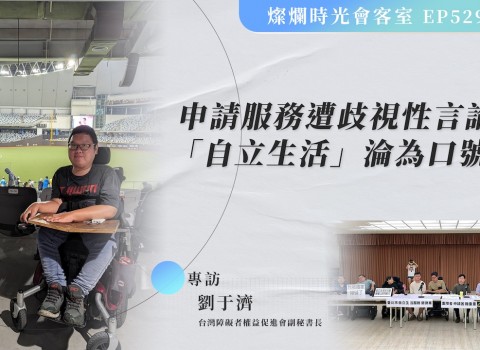文 / 李玥希
相較於台灣,日本更早進入高齡社會,擁有比台灣更完善的長照制度,照顧者殺害被照顧者的案件卻一再發生?為何憾事不斷重演?和鄰國相比,台灣可以借鏡什麼?本集節目邀請到國立台北健康護理大學,長期照護系的陳正芬教授,與我們談談日本長照悲歌與台灣相似之處,以及應該如何改進。
《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為日本NHK調查小組撰寫,在超高齡化的日本,長照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日常。書中提到不同案例,如高齡配偶間彼此照顧、為照護而辭職的照護離職,多種照顧狀況顯示家庭照顧者的痛苦與難處。陳正芬解釋,NHK在本書不只是分析各個案例,更有預防性功能,達到防患於未然的效果,避免發生同樣的案件。日本家庭照顧者殺人的原因有兩個面向,第一種是照顧者看到被照顧者長年的痛苦,心有不忍及無力感,因此選擇殺人;另一種則為平均年齡逐年增長,導致照顧時長沒有盡頭,只能日復一日無限循環,令人感到無助。
改善長照 避免更多照顧殺人
對某些照顧者來說,殺人是為了解決彼此的痛苦,但為什麼照顧會成為痛苦之事?陳正芬說,日本提倡零家庭照顧者,便是希望透過國家的福利資源,讓長照由專業人員服務,而非家庭照顧者獨自扛住照護責任。但實際卻沒辦法真正落實,即使使用居家服務或日間照護,長照人員只會在特定時段服務特定項目,假如一天服務四小時,仍有剩下二十小時以及整整兩天的周休二日需要由家庭照顧者承擔。
陳正芬表示,很多照顧者長年耗費精力照顧家人,最後自己也成了病人,因為資源不足,逐漸產生無助感,無法抽身喘息,反倒成了病人照顧病人的情況,如何不讓照顧者患病?如何讓照顧者得以喘息?節目主持人管中祥提到個人助理制度,個人助理相較長照資源有更多的空間,時間上較彈性,不是框架住照護服務,以固定程序及內容服務每個人,相反的,是因應每個被照顧者的需求,做出個人服務。陳正芬回應,現今社福教育並沒有這樣的訓練,未來需要提供相關的培訓,並謙卑地面對家庭,讓個人助理與長照銜接搭配,減緩家庭照顧者壓力。
台灣長照的課題 司法上的判刑
和日本不同,台灣家庭照顧者殺人分為四類:成年子女殺害父母、配偶照顧者的殺害、父母殺害身心障礙之子女,及手足間的照護殺害。照顧殺人的案件中,有部分的照顧者會在殺害被照顧者後自殺,演變成自殺殺人。陳正芬說,自殺殺人的議題,往往都是照顧者為逃避社會的譴責、對自己做出殺害行為的自責,而在殺害被照顧者後選擇輕生,這其實是社會沒辦法接住照顧者的後果。
在台灣殺人是重罪,殺害父母更是社會文化與道德不允許的行為,刑責更加。照顧殺人是照顧者長期照顧家人,感到無力、沒有盡頭所做出的決定,不該將其視為一般殺害親人之案件,用普通標準判刑。不過,若以台灣的減刑要件來看,自首、精神鑑定以及其情可憫是主要的條件,也就是法官可以視事件不同,給予不同的處分,而緩刑的部分則為兩年以下才能申請。以第三項其情可憫來說,和法官個人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每位法官對於父母、子女、手足在家庭之中的責任皆有不同的認知,判決結果會有極大的落差,在殺害父母之案件中,更只有微乎其微的機會能申請緩刑,在照顧殺人的案件中,從寬量刑的機會非常小。
陳正芬表示,在家庭照顧協議中,長照服務法第十三條便寫道,在成為家庭照顧者後,國家有責任提供照顧者所需要的知識技能與喘息服務,全台目前有超過一百五十個家庭照顧者據點提供服務。即使設立多處據點,許多照顧者仍不會向外界求助,因為這和家庭照顧者如何認知自己的角色有關,一般來說,兒女會認為照顧父母是自己的責任,而非「照顧者」,便不會求助相關資源,擔心會顯現自己不夠盡責。
喘息不是不負責 而是讓生活更好維持
陳正芬說,在企業中,若發現有人因為家庭照顧而離職,應引進長照資源,鼓勵立法家庭照顧假,讓照顧者有互助喘息的機會,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安排照顧,能夠實行至少周休一日的權利。家庭照顧者一旦離開職場,對國家與個人經濟都有很大的損失,期許民眾與國家都能有進步的思想,讓長照介入家庭,避免自殺殺人的憾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