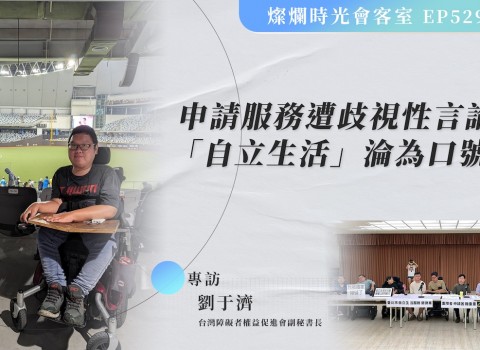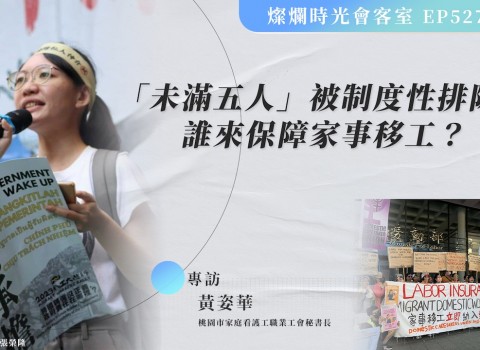文 / 机瑋琪
在這個彈性工時、隨時On call、訊息爆量的時代,「累」成為了現代人最熟悉卻難以言說的感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黃涵榆,長期關注病痛、精神分析與身心困境,近日出版新書《沒有最累,只有更累:倦怠的文化史與精神政治》,以學者視角,結合哲學、社會學與精神醫學等跨領域研究,帶領讀者重新認識「倦怠」背後的多重結構因素。
倦怠的多重決定 倦怠究竟從何而來?
「自己很累,身邊的人也很累」黃涵榆說,身為一名外文學者,他選擇關注倦怠、精神醫學等議題,來自於自己和身邊人普遍感到疲憊的深刻體會,疲憊、失衡的身心狀態幾乎存在於每個現代人身上,過度適應與自我合理化已成日常。
不合理的照顧方案 家屬訴求政府正視問題
一般人提到倦怠,多半聯想到身體不適或四肢無力。然而黃涵榆認為,倦怠並非只是個人身體負荷過量的結果,而是一種由科技、經濟、時代、文化與社會結構等,多重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回顧倦怠作為「時代病」的歷史,從19世紀的精神衰弱,到現代的慢性疲勞症候群、職業倦怠,不同時代都曾以各種名義,描述這種無法言說,卻真實存在的疲憊感。
更麻煩的是,倦怠難以被單一醫療部門完全診治:神經內科、內分泌科、消化內科等,反映越來越複雜的身心狀態。醫療體系對倦怠的認識與處理方式,難以清楚解釋,疲累感究竟從何而來?它神秘而難以捉摸,像是一層瀰漫全身的霧,不僅困擾個人,也挑戰醫療體系的理解框架。
從使命感到自我剝削 對於倦怠的自我辯解
許多高情緒勞動的職業,如社工、醫護或教育工作者等,長期暴露在工作、生活緊張中,投入大量共感情緒,容易成為高風險倦怠族群,導致身心資源枯竭。
除此之外,勞動者也常給自己一杯心靈雞湯,用「使命感」說服自己,因為這項工作很有趣、很有意義,所以值得投入,建構出一套支撐自己繼續勞動的價值觀,但同時也可能演變為自我麻痺與自我剝削。以為自己真心喜歡,實際上是被工作的意識形態驅動向前。
資本主義新精神 更自由也更隱形的疲憊
談到資本主義與倦怠的關係,黃涵榆提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透過節儉、自律與「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財富」的觀念,形塑出勞動者的自我要求。
隨著資本主義的演變,當代的「新自由主義」,更強調多工與自我實現,每個人都是商務人生,隨時保持工作彈性。數位科技模糊了工作與休閒的邊界,疫情時代 work from home,勞動不再只是固定場域,而是隨時隨地進行,辦公桌、咖啡館、甚至是床邊,模糊、混雜的公、私領域,不但使人無法好好休息,更讓人無法察覺自己的情緒疲乏。
資本主義精神與新自由主義,滲透勞動者的深度意識形態,自我麻痺式的燃燒,甚至把「時間管理大師」視為崇高的追求目標。Nike廣為人知的「Just Do It」口號,就是這種永動人生的最佳象徵。
時間的霸權 被切割與計算的生活
不同時代的人會有不同時間計算方式,從日晷、鐘錶,到現代的行事曆與提醒軟體,資本主義下的時間被精準切割、量化,成為強制服從、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從奴隸制度、工廠工人、學童到白領上班族,都在時間的霸權下被規訓。
資本主義下,時間成為可計算與監控的資源,誰掌握時間的價值,誰就掌握霸權,時間成為了貿易生產的霸權科技。標準化的時間概念,雖帶來效率,卻也強化生活作息的規律、勞動時間的分配、社會角色的期待等,種種現代倦怠的根源皆隱藏其中。
倦怠是比好生意?資本主義情感精神
疲憊不只是個人的痛苦,也成為商機。倦怠與其說是該被治癒的症狀,更像是驅動龐大產業鏈的動力。資本主義情感精神,重視情感與感官體驗,人們透過購買情感商品,安頓自己的身心狀態,療癒文化成為對抗倦怠感的暫時解方。
當代社會越來越重視情感與精神層面的消費,不論是心靈雞湯式的勵志書籍、標榜紓壓療癒的課程、冥想APP、心靈諮商與正念課程,或是社群平台上隨處可見的「自我照護」課程,舒緩倦怠似乎成為一項蓬勃發展的產業。
黃涵榆不否認這種消費性療癒文化有其必要,但這樣的消費模式,潛藏著風險。當人們過度依賴商品化的療癒,重視有效率找到解方,可能忽略倦怠背後的結構性原因,缺乏對「為什麼而累」的深入追問,而僅是暫時舒緩,然後再次投入相同的高強度工作與生活模式。
我們該如何面對倦怠?
本書並未對倦怠提供快速或標準化的答案,相反地,黃涵榆希望能帶著讀者自我察覺、自我照料,傾聽自己的身體、精神與情緒傳遞的訊息,為什麼焦慮?從何時開始感到疲累?又為何在喘不過氣時,總是視為理所當然?
在這個「沒有最累,只有更累」的時代,我們或許無法真正擺脫疲憊,但或許可以嘗試理解:究竟為什麼而累,又如何不再只是默默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