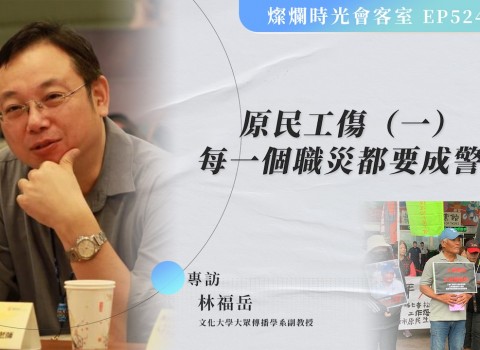文 / 黃馨慧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最近發表了《有歌一起唱——林班歌》專書,委託靜宜大學副教授黃國超,耗時三年跑遍半個台灣進行田野調查與歌曲採集,系統性地集結台灣原住民在林班工地勞作時傳唱的歌謠。
本集節目邀請黃國超來分享團隊在田野調查的發現,林班歌都在唱些什麼?工人們休息時即興哼出的歌曲,如何反映出原住民族當時的生活背景,甚至是他們的被壓迫史?
林班歌:林班工人休閒時的即興創作
林班歌是什麼?顧名思義,就是在林場工作時所唱的歌曲。1960至1980年代中期,當時因為造林政策,林務局會到各地林場附近的部落或村莊,尋找原住民勞力從事造林工作,例如砍樹、植栽、疏伐。族人會結伴上山,一起待在林場工作兩到三個月。每到夜晚,族人們就會圍在火堆旁,一邊烤火、一邊唱歌,消磨時間也釋放感情,這是他們為數不多的休閒娛樂。一人起頭,其他人跟著一句接一句地附和疊唱,玩起歌曲接龍,這種因娛樂而起的跟唱,就是林班歌的詞曲創作過程。
在林班裡被創作出來的歌曲,隨著工作結束的族人下山,帶回自己的部落,被族裡的小輩和鄰居傳唱,有些族人遠赴他鄉工作時,這些林班歌又會傳給其他部落。黃國超補充,在1960年代,雖然已經有音樂的綜藝節目和廣播電台,台灣唱片工業也開始發展,但原住民仍較難觸及這些管道,所以林班歌主要藉由實體聚會,或是族人面對面來傳唱,自成一種特別的傳播形式。更有趣的是,這種大眾媒介之外的非正規管道,反倒讓林班歌能逃過當時黨政單位的禁歌審查,使得各種富有生命力與情感的歌詞都能被保留下來。
從林班到平地 林班歌詞轉變反映青壯年出走部落的哀愁
1960年代的林班歌旋律和日本歌謠、傳統原住民歌謠較類似,因為當時工人只需要上山工作三個月,所以歌詞裡比較少深沈的悲情色彩,唱的多是對家鄉、愛人的思念之情。有趣的是,黃國超透過田野調查發現,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整個台灣社會經濟轉型、加工出口區和大型工業區的興起,原住民青壯年有更多的就業選擇,加上林業政策改變,政府禁止伐木,使得許多族人嘗試離開部落,到平地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一年半載才回鄉一趟。使得這個時期的林班歌謠,內容更多擔憂自嘲,在山上林班工作的族人,擔心自己比不上那些去都市就業的原住民。從林班歌謠的內容轉變,就能看見在當時的時代變革之下,原住民產生的各種焦慮和不安。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不分漢人或原住民,都需要離鄉背景討生活,但原住民又背負更多的無奈。黃國超說,1950年代後,政府雷厲風行推動山地平地化的現代化運動,設下各種檢查項目來規範原住民家裡面的居家設施,或是添購足夠的現代化電器,沒有達標的家戶就會被貼上不及格戶的標籤。為了符合政策規範,原住民背負了更龐大的經濟壓力,使得他們愈來愈多人選擇能賺更多錢的工作,例如跑遠洋漁船,間接導致部落青壯年人口外移、部落勞力空洞化。
流行音樂工業衝擊與族語被污名化 林班歌創作出現斷裂
為期三年的田野調查,除了把數十年以來的林班歌謠更系統化的整理,黃國超也有新的發現。他表示,在調查之前,本來預設能從很會唱歌的阿美族人那裡,採集到很多林班歌謠,然而實地訪問後的結果卻是相反。原來1960、1970年代,阿美族青壯年大多選擇跑遠洋漁業,而不是去林場工作,所以阿美族的林班歌謠其實並不多,但也同樣從勞動生活中,創造出自己的遠洋歌謠。
黃國超也分享,在原住民的林班歌謠裡,能聽到和閩南語歌謠類似的日本演歌風格,加上許多林班歌謠都是用日語或是族語來創作,所以不知情的人,可能會將林班歌誤以為是日本歌謠。
但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推動國語政策,加上原住民族面臨母語被污名化,導致1970年代以後的林班歌謠,迎來一個明顯的語言轉變,有越來越多的林班歌詞使用國語來創作。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感受到族語的污名感,開始排斥用族語創作。
雖說目前在小吃店、投幣式卡拉OK店、教會和社區活動裡,林班歌仍然非常普遍。但黃國超也坦言,林班歌受到華語音樂工業和外來流行歌曲工業的強烈衝擊,80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喜歡有節奏的曲式旋律,林班歌謠已經不太符合他們的胃口,導致林班歌曲的創作產生了巨大斷層,根據黃國超調查,1960到90年代累積的林班歌數量,保守估計有四千首,但這四十年間醞釀下來的龐大音樂資產卻難被繼續傳承。
歌曲作為紀錄形式 林班歌唱出原住民族的改變軌跡
「如果要說林班歌對我們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認為它是戰後原住民族非常重要的時代變遷載體」黃國超說,林班歌謠不僅是紀錄當時林班工人的情感記憶,也蘊含了不同世代族人之間族群創作的記憶。黃國超透過訪談發現,有很多唱搖滾樂的年輕族人對母語並不熟悉,所以會回家請家中長輩幫忙將國語歌詞翻譯成族語。而有些林班歌裡有淺顯的國語,其實也反映了原住民族跌跌撞撞學習華語的過程。
耗時三年,輾轉南投、屏東、高雄、花蓮和台東,黃國超的團隊透過田野調查得到了更多具體的資料,實際訪談後才發現,林班歌的實際狀況和網路與媒體記載的資料都不太一樣。比如大眾較熟悉的『AM到天亮』,大家或許以為原住民都光用一個Am,一直唱到天亮,但透過受訪者的說法,林班裡的作息其實都是早睡早期,並沒有Am到天亮這回事。
黃國超也指出,坊間任何一本有關台灣音樂史的專書當中,都無法看見任何除了傳統音樂之外,和原住民有關的音樂產業紀錄,因為林班歌是族人用母語互相傳唱,聽不懂族語的紀錄者,自然無法深入了解。
若將歌曲作為一種紀錄的形式,林班歌謠也紀錄了原住民族在四十年的變遷裡,所經歷的各種哀愁、無奈的心聲。聆聽林班歌,能在或婉轉、或激昂的旋律裡,看見原住民族配合著社會的改變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