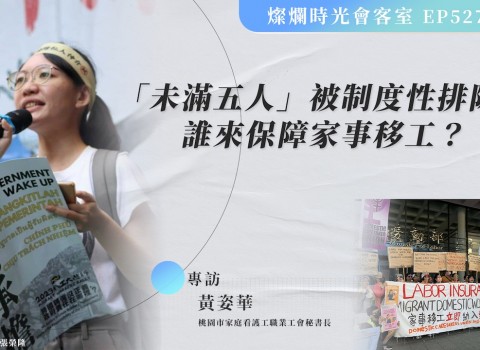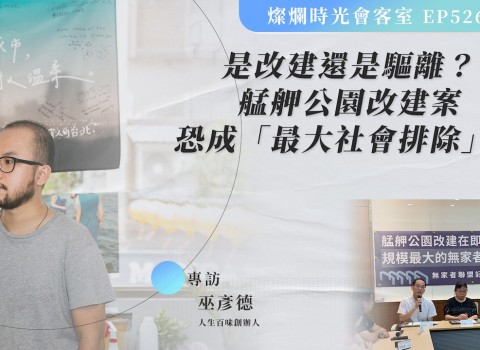在噤聲的時代,有多少人的名字被奪走、無法成為自己的主人?
《禁錮的餘生》不僅是一部關於傳奇女伶高菊花的紀錄片,更是臺灣歷史與時代命運的投射。這部紀錄片不僅還原這位傳奇女性的生命故事,更透過她的經歷,反映出歷史中無數被迫噤聲的靈魂。
從阿里山的公主到紅遍臺北夜總會的高菊花(派娜娜),她的父親高一生因為政治迫害遭到槍決,當時她僅20歲,身為長女只能扛起家計,以歌聲換取11名弟妹的生存,但即使站上舞台,卻仍無法擁有自己的名字。
高菊花是誰?有什麼樣的「傳奇」故事?她的一生投射出什麼樣的台灣歷史與認同?身為「白恐二代」的她,父親遭到迫害,她又受到什麼傷害?又如何看待自己和父親的關係?為何她「終生沒有做過自己名字的主人」?《禁錮的餘生》從企畫、製作到募資,還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野火樂集總監熊儒賢,一起來討論高菊花的生命故事。
時代洪流中的身分漂泊
高菊花是阿里山鄒族人,出生於1932年,於2016年離世。她一生擁有許多名字,卻從未能擁有過自己的名字。她的族名為「Paicu Yata’uyungana」,日文名為「矢多喜久子」。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因日文的「喜久」發音與「菊花」同音,又改為漢名「高菊花」。然而,在她20歲那年,父親高一生遭誣陷為「政治犯」被捕入獄後,又將她改名為「高芳梅」,以改名來祈求未來一切順利,但結果卻不盡人意。
因父親意外入獄,家中頓時失去經濟支柱,為了更多的收入,高菊花前往各大都市的歌廳演唱,在她上台前一刻,由樂團朋友臨時取名,成為大眾知曉的「派娜娜」。
不過,在這樣的時代與家族命運的重壓下,儘管受到萬眾矚目,高菊花卻始終無法擁有自己真實的身份,她的名字總是被外界所決定,從未做回真正的自己。
被遺忘的「派娜娜」
熊儒賢第一次聽聞「派娜娜」的名字,是在2002年《野火樂集》剛成立時。被譽為「台灣第一代搖滾音樂之父」的雷蒙合唱團的主唱金祖齡在訪談中提到,他很思念一位名叫派娜娜的歌手,不知道她是否仍在人世,但金只記得她的身世坎坷。這段話讓熊儒賢印象深刻,卻未特別放在心上。
直到2006年,野火樂集籌備《鄒之春神》音樂專輯,計畫錄製鄒族音樂家高一生生前的創作,熊儒賢帶著忐忑的心情前往鄒族部落拜訪。在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老師的引領下,逐一走訪各部落,高英傑也介紹自己的長姊高菊花,並說她曾在台北歌壇唱歌。此時,熊儒賢才驚覺,這正是金祖齡口中的「派娜娜」。
熊儒賢提到,過去二十多年,許多學者與文史工作者曾多次探訪達邦,研究高一生的歷史,卻未曾有人關注到高菊花的故事。當熊祖賢第一次問她:「你是派娜娜嗎?」或許那一刻,她才回想起,自己不僅是高一生的女兒,更曾是樂壇的「派娜娜」。
尚未成為派娜娜之前
高菊花的一生充滿戲劇性,前半生宛如童話般耀眼,後半生卻背負沉重的命運轉折。20歲之前,她是阿里山「三公主」之一,她與姊妹們因美貌聞名嘉義一帶。連美軍飛行員都曾駕駛直升機,特地從嘉義機場飛到阿里山,只為一睹芳容。
她的傳奇並不止於外貌,她自小便浸潤於知識與音樂的氛圍之中,即便生長在深山之中,家中留聲機播放的是貝多芬的樂曲,父親也時常研讀俄文書籍,讓她養成開闊的視野與卓越的文化素養。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的她,更錄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展現了非凡的才華與學術潛力。
歌壇閃耀的派娜娜
然而,命運的轉折來得猝不及防。1952年,父親因政治案件被冤入獄,家庭頓時陷入困境。作為長女,高菊花成為家裡的經濟支柱,不僅試圖救援父親,也努力維持家中11名兄弟姊妹的生計。
作為派娜娜的高菊花在歌壇發光發熱,她演唱的《夕陽歌曲》大受歡迎,也因此吸引雷蒙合唱團的注意。熊儒賢說,當時高菊花的知名度甚至可以與後來的原住民歌手張惠妹相提並論。
熊儒賢補充,即使高菊花已遠離歌壇多年,仍有來自台南的80、90歲的歌迷送給她一台非常大的電視機。這份來自歌迷的深情深深打動了熊儒賢,讓她更加理解派娜娜在歌迷心中所擁有的深厚情感聯繫與持久影響力。
更殘酷的命運仍未停止。1954年,高一生遭槍決,高菊花的人生從此改變。她原本正處於事業巔峰,卻不得不承受政治壓力,每當她下了舞台,總要面對警總的監視與盤問,時常半夜被帶去問話,直到天亮才被釋放。
唱片公司原本計畫投入大量資金與高菊花簽約,並為她打造更大的舞台,然而,政治因素與其他種種原因,使她未能發行專輯,這也成為她心中的遺憾。儘管如此,她在當時的音樂界留下了不可抹滅的足跡,特別是那些珍貴的影像記錄,成為後人永遠的記憶。
如果不是高一生的女兒
原本有無限美好的未來,因現實的巨變而中斷,這樣的轉折影響了高菊花的一生,使她的名字逐漸隱沒在歷史中,直到今日,外界再度談論她時,卻往往只是「高一生的女兒」,而非她自身的故事。
談起高菊花與高一生的關係,熊儒賢說,高菊花一生中最愛的人其實是她的父親。每當熊儒賢與高菊花喝著小酒,高偶爾會放下阿姨的角色,袒露自己的心聲:「如果我不是高一生的孩子,我的命也許不會這麼悲慘。」這樣的話語揭示了高菊花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掙扎。一方面希望自己不是高菊花,這樣她的生活會更輕鬆,但另一方面又為能成為高一生的孩子而感到光榮。
熊儒賢認為,高菊花是個充滿愛恨交織的人。高菊花父母的墳墓就放在她家中的後院,儘管她的父母已經離世多年,依然獨自居住在達邦部落。熊儒賢有時候到她家拜訪,高菊花會語氣自然的說:「我爸爸剛剛來過了」,彷彿她與父親的心始終緊緊相連,從未遠離過。
傳奇女伶高菊花:不只是派娜娜也不只是高一生的女兒
熊儒賢回憶起初次訪問高菊花,心中充滿困惑:「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現在叫這個名字,等一下又叫那個名字,那你到底是誰?」起初,她只知道高菊花是「派娜娜」,但隨著多次接觸,她逐漸發現了更多與高相關的名字與故事。
在製作專輯《鄒之春神》時,熊儒賢不僅收錄了高菊花一生的音樂作品,還加入了音樂文本《小美說故事》,講述高菊花的生命與故事。經過深入了解,熊儒賢深信,高菊花的痛苦、堅持與成長值得被後人知曉。從此,她每年都會上山探望高菊花,這成了她的一項承諾。
在這段訪談中,熊儒賢總是親切地稱呼高菊花為「菊花阿姨」,談起高菊花的經歷與故事,彷彿在說自己的媽媽。她不時回想起高菊花當時的神情與語氣,並穿插自己對高菊花的印象,仿佛高菊花的身影從未離開過,依然活在她的心中。
熊儒賢認為,高菊花的音樂成就與她一生的波折,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時代的洪流與家族的悲劇共同塑造了高菊花,但高菊花的傳奇並非源自她的選擇,而是命運的安排,使她成為那個時代不可忽視的存在。
高菊花18歲那年,父親尚未被囚禁,她和多數人一樣,滿懷著少女情懷和對異國的嚮往,到電影院觀看美國音樂喜劇電影《一代佳人》(Rose-Marie)。受到電影浪漫氛圍的啟發後,她在日記中為自己取了個新名字Rosemary,這也是高菊花首次也是最後一次為自己命名。
穿越時代與文化的共鳴
在過去十多年裡,熊儒賢曾邀請作家撰寫高菊花的故事,並錄製高的口述歷史,這些努力彷彿是對高的生命與藝術的一種紀錄,希望讓這些故事永遠保存下來。自2016年高菊花過世後,熊儒賢感受到流行音樂界未能對她的貢獻給予足夠關注,這段歷史與文化底蘊仍未被充分揭示。這份未竟的使命感成為她繼續努力的動力。
2020年,儘管熊儒賢已經出版過高菊花的傳奇故事,也發行了名為《派娜娜傳記》的專輯,選用了高菊花最喜愛的舞台照片作為專輯封面,並以金色浮雕設計表達敬意,但在推廣這些作品的過程中,她深刻感受到這些作品的意義遠超過個人情感寄託,更是對高菊花在音樂界影響力的真正致敬。
因此,熊儒賢決定製作這部紀錄片,不僅是對高菊花的致敬與紀念,更是一種情感的連結。高的故事不只是個人的經歷,更映照了整個時代的社會困境。雖然她的一生充滿悲劇,但透過這些故事,後人得以看見歷史的傷痕,理解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並從中找到值得記住與反思的意義。熊儒賢表示,這部紀錄片不只是回顧某個特定時代的故事,更希望讓所有經歷過相似命運的家庭後代,無論來自何處,都能夠感同身受,甚至產生深刻的共情。
突破現實的限制:堅持說出不被接受的歷史
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並不順利,熊儒賢在募資與尋求資源上屢屢受挫。當她試圖尋求贊助與資源時,卻一次次地被現實撞擊,由於基金會與企業只要看到「白色恐怖」四個字,便選擇退卻,即使熊儒賢試圖從女性視角或人權議題切入,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決定。
熊儒賢認為,在文化與藝術領域,若作品涉及歷史、政治與社會議題的作品,則往往被視為敏感而遭到排除。即便試圖透過政府補助尋求支持,最終仍發現自己的作品不在入選名單中,而獲選的則是那些更具「藝術性」的作品。
除了政治性的顧忌,熊儒賢也發現,向原住民相關基金會申請資助時,對方更關心的是是否有親子活動、巡迴演唱會,或能帶來娛樂效果的內容,而非一部講述時代女性如何面對不公與壓迫的紀錄片。再次顯示,社會對於某些議題的接受度仍然有限。
然而,熊儒賢堅信,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高菊花的故事更不該被忽視。《禁錮的餘生》不只是從政治角度切入,而是回到人的情感,讓觀眾看見一個女性如何在時代的壓迫下掙扎、抗衡,並努力活下去。熊儒賢指出,高菊花曾經說過,她不想死,她也渴望丟下所有一切。事實上,高菊花和許多人一樣,只是想過自己選擇的人生,但現實卻不斷將她推向困境,她只能一次次調整步伐,在不公義中尋找出口。
《禁錮的餘生》呈現的,並非一個傳奇式的英雄形象,而是高菊花作為一名女性、作為白恐二代,那個時代面對一連串的命運不公與不義,依然堅強、倔強地活下來。高不是不會動搖,也並非從未想過放棄,但即便如此,她仍選擇活下去,用愛去面對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