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個人都自然而然會知道面對親職困境可以怎麼做。(攝影/何宇軒)
文/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近年來,殺子後自殺的案件屢見不鮮,從紙尿褲男孩到單親媽媽殺子案,今年年初也曾發生一起軍人殺子後自殺的案例,軍人送醫後仍不治。沒有人知道是否因為他自殺成功才沒有受到輿論撻伐,案件也沒有被廣泛地討論,這些案件卻隨著時間逐漸淡化。幼小生命的逝去讓人心疼,而真正面臨育兒困境的家庭數量,恐怕遠遠不止浮上新聞版面的案件。本次廢話電子報訪談國小老師翁麗淑與黃致豪律師,從他們的親職與各自的專業出發,和大家分享他們對於這些案件的想法感受。
邪惡犯罪背後的真相
「我常常在思考如果有哪個時間點,有人伸出援手,會不會事情可能不一樣?」麗淑說。前來訪談前她才將孩子託給朋友照顧,當時就在想,如果吳若妤跟自己一樣擁有好友的協助,可能不會殺害兩個孩子。當看見殺子後自殺的案件,她認為這樣的行為不會只是因為一、兩次的無助和憂鬱情緒,那往往是累積而來的情緒才導致憾事發生。
致豪很同意麗淑的說法。傳統的價值觀會認為,結婚就會懂得怎麼做他人的配偶,生孩子也會自然而然知道怎麼做父母,但其實這麼多的案件中都可以發現,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當我們在投入一個新的社會角色時,需要很多新的職能,比如成為別人的伴侶,家中如何分配職務?當今天要承擔的是新生命的扶養或成長時,責任也會隨之增加。他分享,自己在不同年齡階段對案件會有不同的想法,即使同樣會為這類案件辯護,在成為父親以前,面對案件總是痛苦與憤怒的情緒交加。直到成為父親後,他照樣很痛心,但更想去理解,犯罪者在孤立無援的時候,他有沒有可以打電話、尋求協助的朋友?當他感到不知所措時,政府與社會資源在哪裡?
兩人也提到,在必須顧及工作的情況下,育兒經常需要伴侶或父母協助,因為「足夠幸運」,他們的親職有挫折卻能夠熬過。但這些案件中的父母就不是如此,他們不是曾逢工作與育兒的兩難,就是缺乏身邊能夠作為支持系統的家人朋友。尤其每個孩子的需求不盡相同,遇到父母的應對也有所差異,這些家庭於是無聲地墜落深淵。遇到困難為什麼沒有求助?麗淑分享,自己曾有學生的家人被逼債,她協助家人連絡相關機構、申請輔助等資源,幾天後再連繫家人卻都沒有打電話,她才發現很多時候當事人已經長期在困境之下,連求援所需的溝通對話或辦理手續可能都是負擔,自然沒有辦法知道自己還可以有什麼選擇。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自然而然會知道面對困境可以怎麼做。
照顧者好,孩子才會好
在這類型的案件中,基於孩子與照顧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通常會激起輿論的撻伐,就連法官的態度也可能超越法律,牽涉道德觀念。曾有案件是法官引用《兒童權利公約》來判被告死刑或加重其罪。兩人對此十分詫異,「大人好,小孩才會好,而不是你以為只要責備大人,小孩就會變好,沒有這種事。我覺得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兒童權利公約》要保障的是什麼,」麗淑說。倘若我們面對案件的想法一直停留在憤怒的情緒中,那就算法官按照輿論的風向判處並執行死刑後,也仍會再次面臨類似的問題。真正在意孩子的生存,更應該從案件中抽絲剝繭,理解發生的原因並加以避免。
當人權公約被錯用以作為加重刑責的背書,其實只是凸顯法院對兒童權利與育兒困境的無知。
致豪分析,弑童案件當中,就連絕大多數的法律人可能都會希望被告被判死刑。因為法律人的養成過程不太會去讀到法律以外的書,讓他們在理解案件時缺乏立體的想像和立場交換。致豪說:「在親職的身分之下,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利益其實是共生體。比方搭飛機時,逃生注意事項會說明,當遇到亂流或有危機時,氧氣罩應該先自己戴好,再去照顧其他身邊的人。因為主要照顧者自身的狀態不好時,孩子也不會好。如果在這樣的案件中認為去為被照顧者伸張正義的方式是懲罰照顧者,其實並不符合《兒童權利公約》,而透過這個判決,能夠型塑怎麼樣的社會?對這些仍在現實生活中掙扎的照顧者有所助益?答案是否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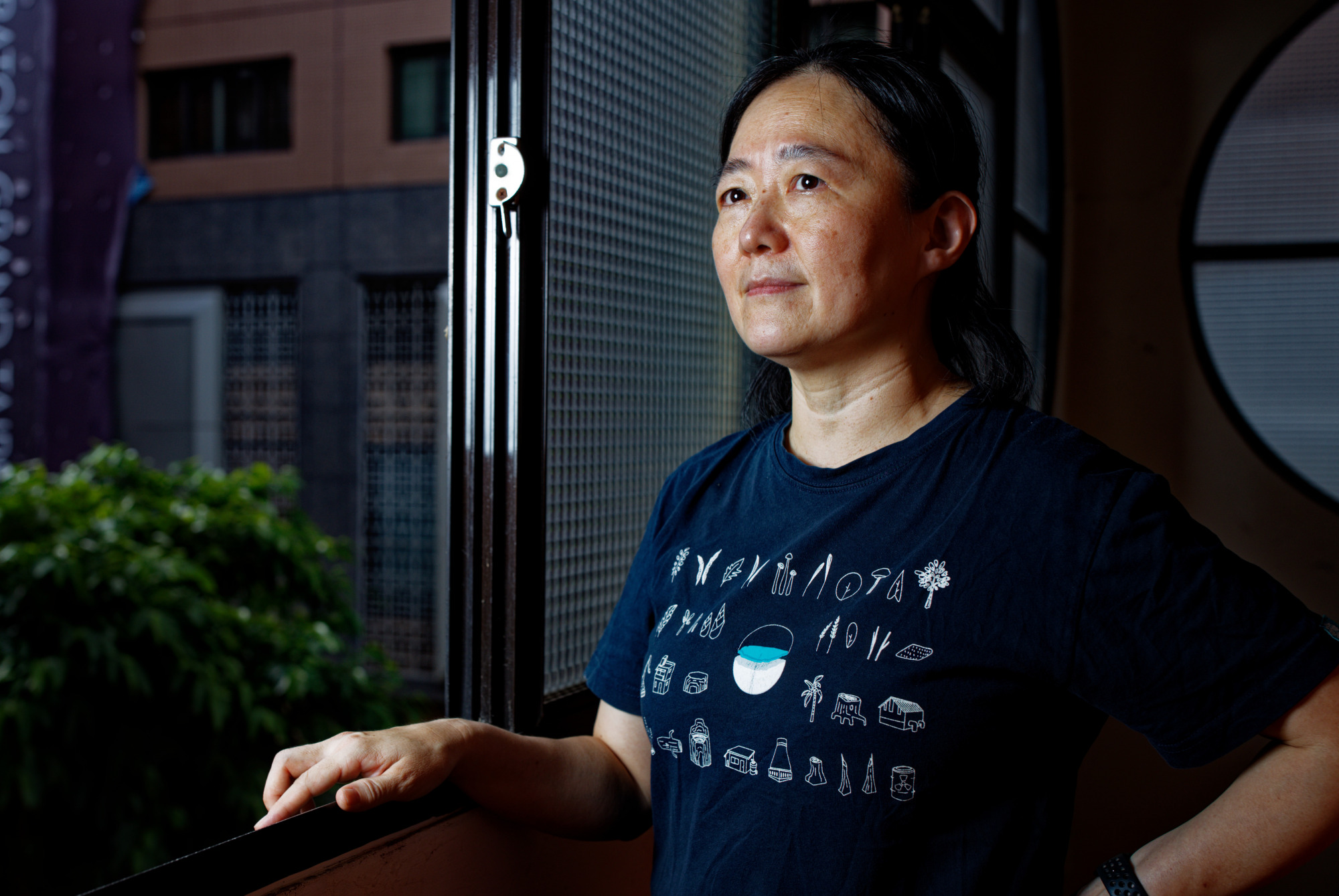
麗淑認為,大人好,小孩才會好,而不是你以為只要責備大人,小孩就會變好,沒有這種事。(攝影/何宇軒)
性別因素在殺子後自殺案件中的影響
麗淑坦承,正因為清楚自己在某些狀況下如果沒有資源,也可能會面臨崩潰,因而在教育者與育兒者的兩種身分中也經常感到無力。孩子的父親曾經辭職,全心照顧家中身障的老三,當時伴侶曾經多次向自己表示,他在白天要帶孩子出門時心裡都有點糾結,因為怕被當做吃軟飯、靠家裡,是沒有用的男人,這跟陳宏嘉案中他所面對的社會眼光有相似之處。如果一個人照顧孩子的過程中無法保留自我尊嚴,一直處於被環境貶抑也自我貶抑的狀態,他不會有辦法善待自己,也更不可能有辦法善待孩子。法官也應該看到這個社會缺乏性別意識,如果法官有看到社會上性別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困境,那麼也許他在判刑上、對一個案件所能夠引起的效應,跟大眾要從判決學習到的東西也才有可能不一樣,而不只是懲兇揚善而已。
自2004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後,學生每一個學期有四個小時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內容包含性教育、情感教育跟同志教育。但麗淑在教學現場發現,大多數老師花最多時間談性別刻板印象,且談的方式是舉例「男生也可以玩洋娃娃」、「女性也可以成為消防員」等。因為這是最安全的談法,也較不容易受到家長針對性教育及同志教育的保守意見反彈投訴,但在無法深入探討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各種幽微的現象與成因時,更可能造成反效果。
當致豪為陳宏嘉辯護時,性別刻板印象正是法院無論如何難以突破的框架。當他要求法院不要把家庭中的男性視為軟弱無力、無能的人時,法院卻問被告「為什麼要讓伴侶在外工作拋頭露面?」、「身為一個男性讓伴侶從事傳播妹來持家是對的嗎?」這樣的說法實質上是直接忽視不同性別在家庭分工中的自主選擇。在殺子的事實之外,法院的判決還要道德苛責被告不符合「身為男性的社會功能」。即使律師請求法官的只是:重新檢視案件的脈絡,一個人為什麼要殺害自己的孩子。但在實務經驗中,法院卻是去問被告為什麼不努力、不做其他選擇。
如何觸及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可以有機會可以做成功的父母,誰想要做這種事?像陳宏嘉、李宏基這樣的案例,如果可以把時光往前推,有人可以去告訴他們有人可以一起想辦法、有人可以協助要求監護權的改判,有方法可以試著重建自己的人生,他們是否就能看見其他可能性?在弒子犯罪、家內暴力的脈絡下,性別刻板印象標籤在法庭上的量刑,讓男性、女性都落入單一功能的期待,而當他們的表現不符合這些期待時,就會被加重刑責。台灣對自殺、毒癮等狀況都設有防治熱線,但在親職卻沒有相關的緊急電話,無論是育兒過程中的情緒、當照顧者本身罹患憂鬱症、有經濟困難,或者當照顧者已經跟原生家庭斷絕聯繫等情況,能夠提供第一時間的引導與協助或陪伴,致豪認為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家庭責任
兩人深有同感,很多時候只要身為親職,不自覺就會有一種概念是:我休息是不對的,我不能休息。這反映出許多最後走向犯罪或自傷的人們,實際上並不是對家庭滿不在乎,而是被家庭責任的重擔壓垮。同歸於盡的偏差思維也是誕生於極端的處境之下,這些案例中的父母,基於社會的養成與期待,終究壓垮整個家庭。
「我覺得我自己也在抵抗這件事情。」麗淑表示。孩子還小一點時,她曾狠下心以看電影為由請託朋友照顧孩子,說出口的當下感到很羞恥,彷彿自己成為母親就應該以孩子為核心,但自己卻打破這個潛規則。她期許照顧者們能建立足夠的「羞恥心」,好好地把自己照顧好,適當求援。真的不是到非不得已才可以將孩子請託給他人,反而要問的是,能不能做到有機會在制度面上達成親職有假期這件事情,可能是一個讓父母沒有愧疚感也不用擔心孩子受虐的機構等等。照顧小孩也不止是父母的責任,而是整體社會共同的課題,去營造不會因為責任互相怨懟的家庭關係。
具備個體邊界意識的親職教育
致豪也觀察到,台灣社會對於親職跟未成年子女之間的嚴重迷思,經常是認為如果愛孩子,就不能放手讓他自己做選擇,將自身的成就與孩子的成就視為一體,要求孩子承受照顧者的所有期待。在物化孩子的理念之下發生體罰,更造成許多社會案件,也有父母因此被認為必須為孩子的所有作為背書或負責。或者有時也會發現,大家對於「獨立」有根深蒂固的恐懼,一方面期待孩子自立自強,另一方面卻不斷干涉孩子的決定,不教育孩子為獨立做準備,卻期待孩子一夕成為獨立的個體。如果有好的親職教育告訴家長「自己是人、孩子也是人」去學習建立健康的界線,適當保護、管教跟引導孩子,也許可以避免更多衝突發生。而當照顧者也能有喘息的空間、合理善待自己,也才有機會建立親子關係的正向循環。
麗淑在教育現場也經常跟家長溝通,孩子的學習已經在學校完成了,回家可以不用再去要求孩子的學業,而可以去發展更多興趣或維繫家庭關係。但很多家長會放不下心,或者有些教師也可能期待家長去要求孩子的課業。當孩子出現狀況,有沒有機會,大家可以一起坐下來真正的溝通、理解孩子的行為是什麼原因、有什麼需要學習的,可以怎麼一起面對?「我常常發現一些無力的父母是,除了更嚴加控管、責罵孩子之外,不知道可以怎麼處理孩子發生問題的狀況。」

致豪分享,如果有好的親職教育告訴家長「自己是人、孩子也是人」去學習建立健康的界線,適當保護、管教跟引導孩子,也許可以避免更多衝突發生。(攝影/何宇軒)
與孩子談論殺子案
許多人將與孩子談論生死相關的事情視為禁忌,致豪與麗淑卻完全不這麼想。「這是社會發生的議題,所以會談。」致豪說。他與孩子們會分享對這些事情的想法、看法,也會交換觀點,比如:殺人為什麼可惡?一個人為什麼要殺人?新聞的描述給自己什麼感受?等問題。致豪認為,討論的過程也是孩子的情緒卸載。透過討論去理解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孩子有機會慢慢意識到有一天自己也會需要面對這個社會,以及事件跟自己的關聯,自己又可以採取什麼行動。這也是孩子重要的學習,而非對社會議題採取必須一蹴可及達成目的,或乾脆認為事不關己的極端態度。
麗淑也認為,如果大人不跟孩子聊,他們反而可能只吸收到新聞或網路報導的片面資訊。在家裡,孩子們會主動詢問,新聞上的事件中有什麼是自己可能還不知道的,常常是在問一個「故事」,而非扁平的追求一種答案或結果,那就有機會產生其他對話。在學校時則可能是孩子們已經先接受了新聞的說法,比如有同學開玩笑稱另一位同學是鄭捷,這樣的事件其實可以打開跟孩子們多聊一聊社會事件的空間,也可以進一步討論當家中出現問題時可以怎麼做、要怎麼建立自己的求助管道等等。在公民、社會課也可以拿實際案例來談法律制度層面沒有補足的部分。
廢死支持者曾經很想殺人的時刻
談及有沒有曾經很想殺人的時刻,麗淑毫不猶豫說:「有耶!在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人或政治人物說了很糟糕的話,或者做出某些決策的時候。」沒想過要傷害孩子,但也曾經很想要放手不管孩子,發生過讓她感到最錐心的是有次不小心對著孩子吼。但這也是學習跟孩子相處的過程,當大人犯錯的時候,孩子也可以要求大人道歉。致豪補充,對孩子表達情緒也是親職技能教育的目標之一,讓孩子理解到照顧者的憤怒跟挫折是基於什麼理由。對照顧者來說,能夠好好表達情緒,除了是維持身心的健康以外,孩子也會學習到尊重自己的情緒。
致豪也表示,在育兒過程中他和家庭很早就擬定親子策略,在孩子一歲半後,就用跟大人講話的方式與孩子溝通,可能也因為這樣的影響,孩子相對穩定。而是否曾經很想殺人?他說,每一天,但他能理解那就是一種情緒。
最後,從殺子後自殺案件談到親子關係,致豪認為,案件反映出暗流底下親職的困境,對於還沒有浮上社會版但即將滅頂、深入泥淖的家庭,仍需要政府與社會去守住最後一道防線。麗淑也和大家分享108課綱中的核心理念:自主、互動、共好。期許無論是在教育或生活中,大家能夠真正的深入了解並實踐,每個人都有機會認識自己並發展獨立的自己,進而學會以適當的方式跟其他人互動,並期待整個社會都能因為互相理解而一起變得更好,而不是相互競爭,互相踩踏,或希望不對的人消失,這樣只會不斷的有撐不住的人往下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