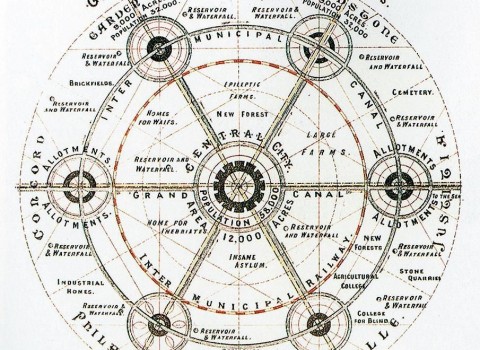(圖片來源:Unsplash)
文/郭彥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我在上篇試圖釐清與保障一種「不必然得聚焦美國帝國」且「重視台灣處境」的左派可能性,但這並不代表我要為那種「一遇到批評美國,就反過來檢查別人是否批評中國,或是否符合台灣利益」的說法辯護,更不是在為那些直接肯定美國的立場撐腰。我前文的立場應該沒有這種傾向,但《左》文所遭受的批評中,八成以上卻正是這類偏狹回應(還有剩下恐怕不到5%的左統批評)。
有些回應甚至耍賴似地說「自己從不標榜左派」、「談標籤已經過時了」,彷彿如此就能迴避《左》文與我接下來要指出的問題。好,就算不談「左派」的標籤,那我們就來談「侵略」。
如果你曾自詡為反對侵略、痛恨戰爭傷害與種族屠殺的人,曾經聲援烏克蘭、嚴厲批判中國的擴張野心,甚至因此輕蔑某些台灣或歐洲左派的沉默與無力,那面對巴勒斯坦至今仍在發生的屠殺,你是依據什麼原則衡量自己發言的多寡?又如何判斷自己的論述是否足夠「有力」?
或許有些人會因此修正立場,認為不應以發言頻率和比例來審查他人,畢竟人各有關注焦點——只是這種主張往往只在自己偏好的立場遭檢查時才被提出。那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看,觀察人們在面對特定政權時如何發言。
多少人在他人提到中國或俄羅斯時,會認為若不談其侵略野心與窮兵黷武,就是替侵略者擦脂抹粉、成為共犯?但在面對美國與以色列時,又有多少人維持同樣標準?是否也願意質疑本國總統偏袒以色列的言論,或批評那些無視川普當天開發加薩地產言論、卻大談其關稅政策的人?若是普丁發表侵略性言論的同時,媒體報導其其他政策而避而不談,是否會立即遭批?那川普呢?
我始終認為,一個關心兩岸、中國或台灣的左派,完全可以把批判甚至打倒中共政權視為政治實踐的核心。《左》文提到左派對中國的分歧,「有的人認為中國已經徹底走向國家資本主義……至少正嘗試往帝國主義發展」,我不諱言這也是我目前的傾向。在這前提下,一個左派專注批判中共,未必就違背左派價值。當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本身就是我認為應該被左派批判乃至對抗的。
我也反對一些統左在中國議題上的雙重標準,譬如在亞亞的案例裡,會強調「國安不該是可以基於言論驅逐人的理由」的那批連署人裡,有多少人會捍衛或替中國以國安為由的言論管制緩頰?看環球人物最新一篇對亞亞的專訪,果然就只強調家庭團聚,武統部分只說是莫須有,言論管制的部分更是隻字未提,一句「有些離別,比槍炮更震碎人心」令人啼笑皆非,彷彿槍炮不會造成骨肉分離。
那衡量的關鍵究竟是什麼?人都有關注的限制,真正重要的是,當你面對不同經驗與質疑時,能否維持原則,而不是扭曲信念。就《左》文所引發的批評來看,「美國」確實成了一個試金石——是否反對侵略、屠殺、海外戰爭與軍事化,在這裡就一目了然。若你堅信這些原則,那他人呼籲更嚴正看待美國帝國主義,自然不該令你惱火,也不該直接被解讀成親中。
誅心式批評不但無助對話,反而暴露討論風格的惡質。指責別人是出於惡劣心態才會說「屎難吃」,也不會讓屎變得好吃。怎麼看待美國的問題,終究是一種紮實的拷問:若你總願意因中國的所作所為進一步批判他人,那當被指出美國也有同樣甚至更惡劣作為時,卻選擇逃避、不肯用同一標準對待,那就乾脆承認——你其實沒那麼在意那些理由本身,而是更在意中國與台灣的利益。承認這也同樣沒什麼。
正因台派對中國惡行已建立一套極為寬鬆的「共犯」與「支持暴政」劃分標準,使得只要稍具美國帝國主義認識的人,看見台灣主流言論時,往往也能依此邏輯解釋為替美國擦脂抹粉。從《左》文一出便遭遇大量「怎麼沒談中國ABCD」的批評可見,即便是在反侵略議題中試圖苦口婆心說明美國角色的《左》文,其質疑方式仍遠比當下對左派的道德審查寬容得多。
「怎麼沒談XX」這種起手式被左派批評者用得樂此不疲,卻往往只是為了逃避真正回應左派所提出的問題——如同許多人嚷著「聲援亞亞怎麼不聲援富察」的人,不會因為羅世宏、郭力昕或盧倩儀等人聲援過富察,就反對貼標籤、正視其言論,而是改成質問那其他人呢?其他議題呢?「中國ABCD」只是被用來無限延宕左派所拋出的質問。
如本文反覆強調的,人有關懷偏重本非問題,問題在於有人對自己的偏重總能寬容解釋,對他人的偏重卻口誅筆伐。尤其有一類人,對於「只批中國」或「只批美國」的言論採取截然不同的標準,卻還自稱「兩者都很重要」,這些時常掛在嘴邊說「美國也有問題」的人,其實最常見的反應卻更像是:「沒批中國就不能批美國」。若你真認為中國問題更嚴重,那也沒關係,但至少該認清自己是在以此為依據調整檢視他人的原則。這點應該被清楚拿出來辯論,而非遮掩。
***
《左》文用了「隔壁惡霸」和「更大尾流氓」的比喻來對照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若換作我來說,我會形容是隔壁會家暴的流氓,和一個歷史更悠久、規模更龐大的黑幫。你每天出門都看到隔壁流氓作亂,要說自己痛恨暴力犯罪,致力對抗,當然沒問題。你因此發展出一套反暴力理論,宣稱所有支持暴力犯罪的人都該死,也可以。但當你發現家人其實會付保護費給那個黑幫時,是不是該重新考慮這個「所有支持暴力犯罪都該死」的說法?你可以承認自己當初話說太滿,也可以誠實地面對現實處境,承認家人的選擇有其為難之處,雖可批判,也期待找到出路。就是承認:你雖反對暴力犯罪,但在生存前提下也有自身的有限和參與。
但如果有家人聽你過去一番「暴力犯罪多可恨」的發言後,認為我們好像也不該繼續付錢給黑幫,甚至不該幫黑幫做武器、拍宣傳,畢竟黑幫做的可怕壞事很多,結果你卻立刻大罵這家人蠢、壞、怎麼不去給流氓打死,還檢查他提到流氓時是不是口氣不夠激憤,或者沒有每次罵黑幫時也順便罵一下流氓,就斷定他跟流氓有勾結、支持暴力,主張要透過家規把這人趕出去。與此同時,對另一批滿口稱讚黑幫老大「多威武、多有謀略」的家人,你卻體諒萬分、從不批評,甚至把他們誇黑幫的話貼在牆上,還幫著解釋:只是稱讚老大的優點,不代表支持黑幫的暴行嘛。到了這時候,還要強調自己當然是個反對暴力犯罪的人,那不是幻想或無恥,還能是什麼?
看到有人批評《左》文拿蔣介石的「抗中保台」當例子是錯的,理由是蔣要保的是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好,這個批評我可以接受。但我也想確認一下,這些人在前陣子亞亞事件中,是否也同樣清楚指出:「意圖顛覆國家的言論/行動不應受到保障」這話裡的「國家」,講的也是中華民國,而不是台灣?還是說,從什麼時候開始,捍衛中華民國就等於捍衛台灣了?從放棄反攻大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還是從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開始?在那之後,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名鎮壓任何可能顛覆現行憲政體制的行動,就變成是在「保衛台灣」了?我只是想問,講這些話時,能不能和你所認同的白色恐怖平反、台獨與華獨區辨、乃至主張推翻中華民國憲法、住民自決、建立原住民族主權的各種論述自洽?
***
總之,雖然我前面花了不少篇幅與《左》文商榷,希望建構一種兼具在地意識與國際關懷的左派可能性,但這並不代表現在超過八成以台灣為本位的轉貼批評,就自動等於這種平衡良好的左派立場。許多批評無非是指責「不夠批中國」,但要判斷這是否成立,其實也不難——就拿《左》文一開始提到的國際交流情境來檢驗。
我們就先不談「左派」這標籤,只談「反對屠殺」。當今全球最大規模、且獲多數國家默許的軍事屠殺正在加薩發生,並得到美國史上最多的軍事資助。若在國際交流中只關注這件事,是極有正當性的。你當然可以回應說中國也在做類似的事,也該被關注,來試探國際友人的價值立場。但同時,也該反問自己:若你在關心中國人權時,會從對方談中國的語氣、深度來判斷他是否「夠關心」,那就請你也把自己過去轉貼所有談論到美國拿來比照一下——這樣看起來比較像是「反對屠殺」,還是比較接近「默許縱容屠殺」?
再舉兩個例子就好。一,美國侵略伊拉克早已證實是基於虛構證據,對當地人民(包括反對海珊者)造成巨大傷害。請問達克沃斯訪台時,有多少人曾轉貼讚揚她是「戰爭英雄」、「神力女超人」?她參與的是哪一場戰爭?你能支持這些說法而不反省,還能理直氣壯地說:因為我很反對中國軍事化,所以我是一個反侵略者?
二,美國號召入侵阿富汗,累積多起蓄意殺害平民事件。澳洲媒體揭露本國軍人屠殺平民,還遭警察搜查;但因為中國外交部用了擺拍圖來批評這件事,有多少人反應是「台灣人應該買澳洲紅酒來力挺」?然後還可以自稱:我很在意戰爭、平民屠殺、新聞自由與吹哨者保護?
這些問題,其實根本不需要和「左派」這標籤綁在一起。認不認同左派無所謂。但在一邊痛批紐約時報等歐美自由派/左膠被龍應台那類說法吸引的同時,不妨也反省:我們平常轉貼、按讚的那些發言,若拿去給 GenAI 翻譯比對一下語境,會不會在價值觀上,其實更接近保守排外的極右派?
那些不斷主張要「提高戰備」、「國家安全優先」的人,很少願意承認,自己幾乎每一條論述都可以被中共完整複製,甚至有美國過去種種黑歷史做後盾(更別提川普對加拿大、格陵蘭的言論所創造的新現實)。除非你根本就不同意原文所說的——美國是歷史上也是今日對世界投射最多軍事暴力與威脅的國家——那就來辯。
但若無法反駁,卻又無法接受任何批評美國的聲音,那是不是該想想:這種「先檢查你有沒有夠批中國」的反應,憑什麼可以這麼理直氣壯?是因為揣測本文作者人在台灣?用中文發表?還是更糟,是因為預設作者的血統和國籍是台灣人,就「應該」優先批評中國或優先考慮台灣處境?為什麼我們一定得接受這種近乎胡攪蠻纏的邏輯:你要是沒夠罵中國,不是壞就是笨?而如果這種要求在面對「國際友人」(假設《左》文作者不是)時你自己也不覺得站得住腳,那是不是該承認,這根本不是一種信念或價值的檢視,而是一種愛國忠誠的審查?
苦勞網的南方國際編譯刊登過不少批判美國、以色列、俄羅斯、葉門等地的文章,平台的選譯方向可以被批評,但拿「怎麼沒談中國的 ABCD」來質疑每一篇文章的作者,合理嗎?如果那不合理,卻對《左》文可以這樣用,那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國籍、血統預設,才會覺得這樣就可以跳過對其內文所提問題的真正回應?
還有一種更誇張的評論,是拿像《左》文這類想當左派的作者來說:若他身在中國,因為主張左派價值、甚至肯定某種「左獨」,那就只能進牢裡當左派。許多自詡為批判中國威權的人對此覺得好笑,但我實在不明白,這種恫嚇怎麼能被當成幽默。
當今的言論空間正不斷緊縮,從中國長年的言論管制,到近來美國的驅逐出境風潮、社群媒體也得字斟句酌。如果你真心認為台灣保有的言論空間是可貴的,那不是更應該堅定地說:所以才更要講出這些話嗎?正因為「批判美帝」這類言論在中國也只能被選擇性呈現,我們才有責任證明,一種更寬闊的批判是可能的。
我選擇公開具名,而《左》文選擇用粉專發文,個人考量或許不同。但《左》文談到左獨團體,甚至把「當美國第 51 州」與「與中國統一」並列為可能都是出自愛台灣的認同形式,也清楚主張「住民自決原則應該落實」。難道作者不知道,這些話在統左群體、甚至中國官方眼中會被視為什麼?但他仍選擇在一篇強調美帝批判的文章裡說出這些立場,結果不只被扣紅帽子,還要被嘲諷「會被中國抓去關」,這到底哪裡好笑?我是真的笑不出來。
說到底,我在這兩篇文章裡努力想證明的,是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關注與信念,不掛「左派」名號也沒關係。但人都有侷限,遇到無法處理的議題時,選擇承認自己的為難、選擇擱置、選擇沉默,這些都沒什麼可恥。可怕的是:為了攻擊自己想像中的敵人,竟變成一個價值扭曲的人,甚至拿著自己曾經最想批判的東西,轉頭去傷害別人。這,大概是這波討論裡最值得被記下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