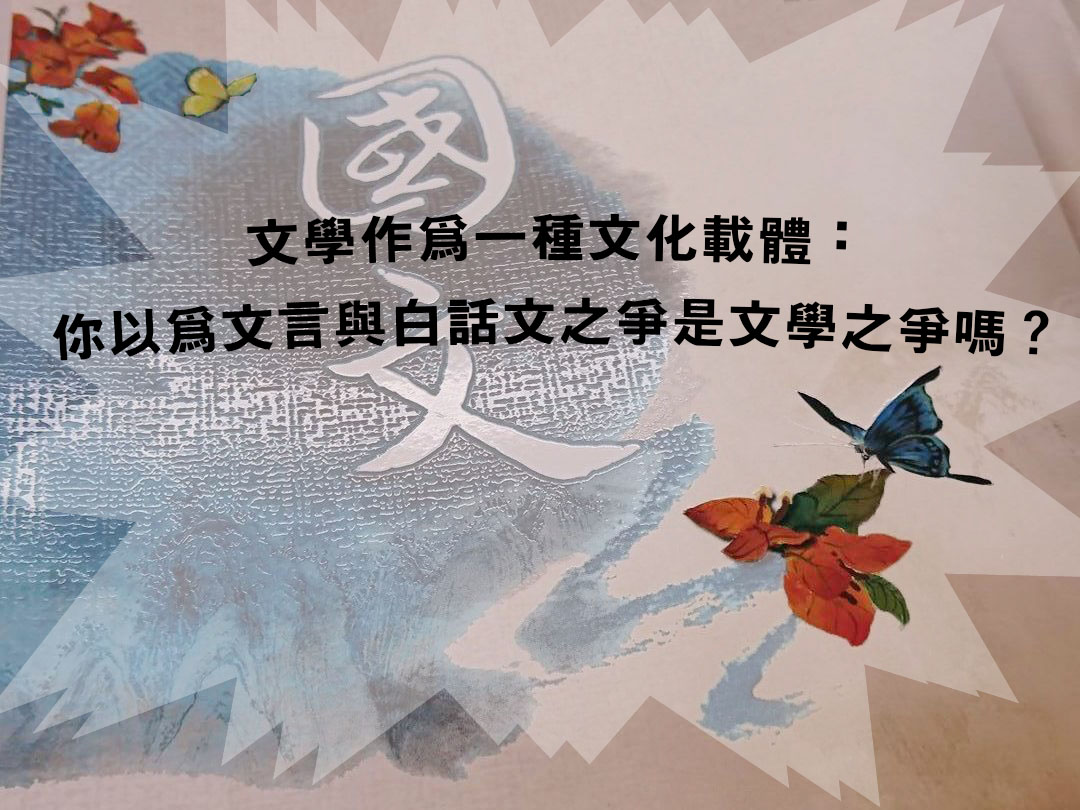文/莊珮柔(建國高中歷史科教師)
近來吵的沸沸揚揚的文言與白話文之爭(以下簡稱為文白之爭),提升到了文學之爭的層次。有人認為這是台灣與中國文學之爭,或是古代與現代文學之爭,甚至連張我軍(1902─1955)先生都搬出來了。
說真的,看到2017年這次的文白之爭談到文學的層次,是令人感動的。語文與文學教育終於在這個年代被人重視,看起來是時代進步了。不過,如果把文白之爭拉到中學教育的場域來,中學課本為什麼選這麼多的文言文,文學其實沒有這麼重要。至少文學之美沒你想像中的那麼重要。
簡單的說,中學課本選那麼多的文言文,基本上就是特定階級施展他們的文化觀與權力,透過教育去傳遞特定的意識型態而已。而國文課本大量的文言文選文,不過是一種民族主義、階級、文化的載體。從中學文言文選文的發展過程來看,大量特定的文言文選文列入課本,透過統治者與課綱委員意志,將選文實踐在中學教育中,其實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產物。接下來,本文將時間拉回1967年,檢視事件發生的經過,討論這個說法。
國文科在中學一直是一種特別的存在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階級是「地位群體」的概念,認為除了通過經濟狀況劃分以外,還必須通過身份、榮譽、價值觀、生活方式的自我認同才能成為階級。特定的身分榮譽與價值觀,當然是透過特定的教育體系複製文化觀,才能展現出來的。
在台灣中學教育體系內,國文科一直是特別的存在。首先,國文的老師授課時數比其他科目少兩節,據說是因為有作文(可是英文也有作文,就沒減課)。而且他們除了必修國文課高中20學分(英文和數學只有16─18學分)以外,2017年為止,國文老師還得兼上必選一節課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時數比其他科多、老師聘任數目比社會自然科多。國文老師可以說是中學老師的主幹,學校內國英數三科人數眾多,一個學校內以國文老師最多。中學擔任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等行政教師,能管理老師,向教育局與教育部反映教育人員對政策、學校管理、學生事物的人,多半也是國文老師,「國文老師治校」在中學裡相當常見。
在學校制度與結構上,國文教育為何擁有如此特別的地位呢?這先得從國文課在中學誕生的經過開始談起,九年義務教育出現在1967年8月17日,由當時蔣介石總統一紙命令,提高到國家安全層次就施行了──〈台統(一)義字第五零四零號〉:「茲為提高國民智能,充實戡亂建國力量,特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四項之規定,經交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第三次會議決定:國民教育之年限應延長為九年,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先在台灣及金門地區實施。」。
九年義務教育的推行,中學的國文課有特殊的任務。其中「民族精神教育」、「文化陶冶」尤其重要。1979年5月8日政府制定的《國民教育法》,第七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採九年一貫制,應以民族精神教育及國民生活教育為中心。國民中學應兼顧學生升學及就業之需要,除文化陶冶之基本科目外,並加強職業科目及技藝訓練」。國文是「民族精神教育」「文化陶冶」的基本科目,現在不少人都讀過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也是在這背景訂定於課綱中。國語課(小學)與國文課(中學),就是中華民國「民族精神教育」、「文化陶冶」的重點科目。
國語還是國文?
現行的普通高中課程國文科綱要,中學的國文教育兼具有「有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文化教育」三個目標,小學是「國語教育」到了中學轉為「國文教育」。還原到1967年-1969年九年義務教育實行時的背景來看,九年義務教育的施行,與同時期的中華文化復興的推廣運動,很快地就跟國文教學結合起來。國文在課程與教學時數上取得優越的地位,與當時政府要把國文教育拿來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載體,是脫不了關係的。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又稱為「文復運動」,是蔣介石總統本人發動的,在1966年11月12日陽明山中山樓的落成典禮時,總統宣布要在1967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這是一種政治對抗,為了對抗對岸的文化大革命。文復運動,就把國文的文化教育看作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1967年,文復運動開始推動不久,中學國文科就誕生了,甚至還想要改小學的國語科改成國文科,一起來文化復興。這些主張以國文科當作是文化復興運動的學者,以歷史地理學者沙學浚(1907─1998)為首,主張將小學的「國語科」改為「國文科」,把國文當作是文復運動來推行。說起沙學浚,他可以說是現在中學國文科的「國父」。如果沒有他,現在中學國文科大量選文言文,選特定意識形態的文章,無一不受到他的影響。沙學浚也率先提出,中學國文科應該教文字、文學、文化的說法。這個說法一直保留在普通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裡。沙學浚不是中文系出身,他江蘇泰州人,小時後受過私塾教育,曾習四書五經。擔任過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63─1972年先後任師大學教務長、文學院院長。他的學生很多,且當時的師大是公費分發的,是老師製造中心,自然影響深遠。
把國文科當作文化復興運動來推,當時也有主張語文教育的人對此產生不滿。有人主張白話文為主的國語派,以為中國語文學會成員和國語日報編輯部為中心,這些人多半有受過西方現代教育學的背景。雙方在1967年互相在報紙、學界,以及國民黨的中常會議中辯論,這是當時最大的語言教育政策辯論。
中學國文科的誕生:國文課本來就不打算只教你語言
受過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讀者,對於中文課程的名稱,記憶中的課名是什麼?中文課的課名,小學好像叫做國語課,到中學則被叫做國文課。國語和國文的差別是什麼?不都是中文課嗎?聽到這個問題,一般人一時之間恐怕也想不出來有什麼不同。這一字之差,其實就跟人生的很多「BUT」一樣,很有意義。
為什麼中學要叫做國文課,國小要叫做國語呢?我們都覺得國文課最重要的功能是語言教育,不是嗎?其實不對。語言教育,在近代國家本來就不是純粹的教你語文之美,沒有語文歸語文,政治歸政治這種事。我們現在以為語言教育跟民族主義、文化的關係應該不大,是教學生閱讀理解、說理、表達意思之類的事情。事實上,語文教育與民族國家常常是息息相關的。
台灣史上曾歷經兩次重要國語運動。一是1945年前以日本語為基礎推動國語,二是戰後以北京話為基礎推行國語。在初等教育推動統一的國語為必修課程,說起來都是因應殖民國家與遷占者統治的需要。國語本是民族國家的產物,19世紀歐洲主要的民族國家,完成建國的大業後都需要統一的國家語言。這跟19世紀末標準德語、法語、義大利語的要求應運而生的道理是一樣的。日本在台灣統治需要推動國語教育,國民政府亦然。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阿勤說,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國語教育是國民黨以「將臺灣人中國化」為目標。
就觀察中華文化在語言、文學、文化傳承的結果來看,台灣的國語教育與國文教育是空前成功的。曹逢甫(Tsao, 1999)則說政府在小學大力推行國語運動以後,對其它本土語言都一致產生負面影響,另外還產生了:文化斷層、人際疏離、族群認同、語言衰亡、弱勢語言文化的衰亡、國家認同的模糊的現象。小學的國語教育摧毀了台灣的本土語言。很多研究都顯示,政府的作法非常成功。中學國文教育則將中華文化載入台人的意識形態,原住民語言在70年代開始大量的流失、台語與客語的流失,無一不是九年國教出現會拿來考試的國文科教育成功的結果。
為了升學,大家都來背文言文,沒有人要學母語。透過國文課,認同中華文化與中華民國,文學之美只是點綴。在義務教育的階段,你懂多少文學之美不是重點,透過特定的選文與升學考試讓你認同中華文化才是重點。國文科選文跟三民主義選文也很像,都得服從「民族精神教育」。
1970年代國文派的美麗世界:文言文與清末民初私塾教育
1967年的時空背景下,難道沒有教育工作者想捍衛語文教育,站在現代教育的立場嗎?當然有。
1967年至1969年間,和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運動同時進行,一方叫做國語派,他們主張初等教育兒童全部說國語用注音,主張多教白話文,說寫一致,又稱為「言文一致」。這一派在台灣小學教育影響很深(也促成現在台灣本土語言衰落)。國文派,在1970年代力主維持文言文教育、主張教經學,維持私塾教育的,他們對語言與文字的統一沒有太大興趣。他們的說法與作法在小學教育沒有被採用,但他們在中學國文教育裡成功了,讓中學國文課本教大量的文言文、恢復經學註釋與考試的傳統,講解古文的這一套教學方法。中學課文內置放入大量清末私塾教育使用的古文,要中學生背經書,很成功地恢復以往清末民初中國私塾教育的教法。
沙學浚和一群看重「文化教育」的學者,在台灣教育界中發動了國語/國文論戰,他們希望把小學國語課也課程也改為國文課。「國文派」主張恢復傳統私塾教育,認為學校裡應該多教「文言文」,主張經典復古、講經(四書)。「國語派」肯定現代語言教育,認為語文應該教白話文「先語言後文字」。兩方競爭的結果。國語派固守國小的地盤,國文派守著中學教育,棄而不捨的註釋訓詁解釋教古文。當時的國文派,也罵國語派,說他們推白話文沒有必要。
如果按國文派的想法,台灣方言盛行是沒關係的,反正大家都寫文言文就好了。白話文運動推行北京話也沒有甚麼必要,就維持清末民初那樣大家各自說方言就好了。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到此也可以結束了。
問題在於意識型態而不是語言:白話文也可以是統派的語言
在論戰中,支持要國語派的人,說「言文一致」(白話文)的意識形態,是統一語言也是統一國家。趙友培在〈國語文教育與文化復興〉(1967)點出國語運動是從「書同文」進步到「語同音」,國語運動是國家統一基礎。另外,趙友培也說「國文」也不等於文言文,「國語」也不等於白話文。張希文表示統一語言才能夠達到「言文一致」,國民的精神才能夠齊一。張認為「言文一致」象徵進步和統一,「文言紛歧」象徵落後和分裂的意識。這一場論戰持續數年,後來支持國語派了力量占上風,國小維持了國語課的名稱。
1967年─1969年論戰時,不論是國語派或國文派,在政治立場上都是統派。兩者不同的是,提倡國文派,則是帶著要執行文復運動的使命。1967年9月、10月間,沙學浚參加教育部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的會議,不諱言的直接在教育綱要指出他要執行蔣介石總統的使命
沙學浚也講了他對國文教育的目標的看法,沙學浚〈國民學校的的「國語」科應正名為「國文」〉(《小學國文證明論戰》:1975)一文中說,他認為教育部訂課綱「應奉行總統『國文第一』的訓示,而推行國文才能適用於方言複雜,且一向用方言教學的區域;若主張「國語第一」則僅適用於北方官話區。」、「中國是高文化國家,有文字,當然要教國文。」、「將「國語」正名為「國文」也代表將教材教法回歸私塾教育的傳統,才是復興中華文化」。在這樣的概念裡,統治者重視文化多於語言,因此中學國文課恢復民初私塾教育裡曾取用的教材,四書五經叫做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拿來教、加入文學上喜歡的文言作品與古文八大家,慢慢發展出1980年代的國文教材,一直影響到今天。
國文教育的非常文化與政治
這場辯論裡。國語與國文教學的改革、政治與教育間的關係,非常赤裸裸的一再被提及。對「言文一致」的思考的目標的相關討論,爭奪的是「中華文化」解釋權,內容甚至延續了民初五四運動以來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兩方都不吝惜表現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的看法。
這兩派人馬在《中央日報》、《國語日報》、《學粹雜誌》、《中國語文月刊》發表文章。沙學浚想藉由教育和文化政策的變動來改變學校的語文教育。他在〈國民學校的的「國語」科應正名為「國文」〉中,提出國文課程的三個內含:一、 「國文」包含文字、文學、文化三方面。二、「國語」科的教學目標中,「讀書」、「作文」、「寫字」都屬國文;唯一屬國語的「說話」則是前三者的基礎,亦可歸入國文的範疇。三、中等以上學校都該以「國文」為科目名。跟今天國文課綱裡提出的文學經典這種說法不同,1967年國民義務教育推行,當時中學的國文課,復興中華文化才是重要的內涵。
1970年代,當時主張文言文教育的學者,很多都是學古文的,自己也受過私塾教育。如國立政大中文教授,訓詁學學者杜學知(1912─),他在〈「語」「文」之辯〉(1968)把文言文的減少當作是文化危機,提出文學的美在於修飾和洗鍊,白話通俗而無文令人不屑一顧。而「言文一致(我手寫我口)」的語文教育為了說話和認字而重白話,輕文言,最糟則可能造成文化的斷絕。1914年生,幼年受過私塾教育,當時的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委員陳邁子,認為輕視文言文的教育會讓學生喪失愛國心、自尊心,進而重洋媚外,而陷文化於死地。因此,文復運動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將小學國語改為國文,才能挽救文化的根基。陳邁子將文復運動與語言連結,認為強調語音的統一將損害固有的文化傳統,並指出文字的統一才是政治統一的基礎。
這些說法,說明當年推動國文教育的人,絕對不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他們相當懂得文以載道,懂得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他們都將文學、語言、文字、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都綁的死死的,也樂於使用國家機器貫徹實踐自己的意見,沒有在避文學和政治的嫌疑的。他們所推動的文言文教育。多半和自己幼年受過的私塾教育有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和他們自己受過私塾教育的經驗綁在一起,他們想復興的,是他們理想中五四運動前的美好中國文化。推動的這群人多半受過私塾教育,他們的童年其實都沒有現代教育的經驗,最多是成年以後再去西方讀書的。
文言文「不口語」嗎?又文學在哪裡?
1967年11月4日國學大師林語堂在《中華日報》發表的〈論言文一致〉一文,林語堂指出一般人將國語、白話、口語三者畫上等號,但他認為這個觀念過分區分白話與文言,國語、白話文、文言文、口語其實都是相通的。文言文也是國語,平時口語也會說文言文,比如說成語。林語堂談到,民初五四運動時期,當時的青年人為何討厭文言文?是因為「咬文嚼字先生賣弄生僻典故的壞習氣,用字以艱深為典雅,以淺顯為鄙俗」。而且這樣的文學,專注於辭藻,反而讓文章全無內容。
林語堂的說法,說明了其實文言文也可以很口語,充斥典故與陳腔濫調,讓文言文也可以不文學。儘管支持言文一致,林語堂滿珍惜文言文的這個古代遺產的。還認為應該教小孩子多用成語,讓文言文變成「文人的國語」。林語堂、沙學浚這一票國學大師大多受過傳統的國學教育,他們都學過精美、文辭豐富的優美古文教育,而且也會寫。他們對語文教育的看法,其實和1970年代以後的語言教育是不一樣的,是一種混合了傳統與現代觀念的產物,與來自現代西方的語文教育看法不同。
現代人說話是給現代人看的,不是給古人看的
在這場語文論戰中,國語實小第二任校長提出了現代性的看法。出身英語教學的王玉川,針對沙學浚的想法,逐一用西方「現代」的語言教育觀念,去反對傳統私塾教材與教學觀念。王玉川認為私塾教育裡的《三字經》、《千字文》等童蒙教材,內容冗長不適合兒童。另外,經學背誦長文的教學方法也違反現代的教育原理,西方語言教學要求兒童學語言應該從完整的短句開始,再慢慢加長。他批判沙學浚將「語文能力」和「知識學問」混為一談,現代語言教學是將「語文能力」和「知識學問」分開學習的。王玉川也強調現代人說話是給現代人看的,不是給古人看的,所以不需學古代人的文言文。
王玉川是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委,他要小學老師自己編課本,因為以前的小學低年級課本沒有注音。因此他的國語說話教材教法,就找了一群國小老師用注音自編課本。後來政大教授祈致賢擔任國語實小第三任校長,繼續王玉川的作法,他們把國小低年級的教材全部加上注音來寫,也就是注音加上中文。這種作法降低國小低年級學生學語文的難度,國語課本全部注音之後,小孩子的語文程度變好了。因為教材容易學多了,克服中文字不容易學的困難。
文言文是特權階級的特權教育
祈致賢注意到,私塾教育其實帶有精英階級的傲慢。他批評國文派,傳統私塾教育,是用於「特權階級」的教育,絕不適用於國民教育。在現實環境的限制下,為推行國語而犧牲辭藻華美的文言文是合理的。
回到1970年代的時空來看。文言文、文學不過是作為一種中華文化的載體,你以為文言與白話文之爭是文學之爭嗎?在當時,文言文與經學,一直是被當成文化與民族教育的載體。特定知識階級在清末私塾教育的經驗,構成文復運動,召喚他們童年的記憶,傳遞著特定階級的想像中的中華文化。這個文化。甚至在中國,已經被五四運動的繼承人: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革掉了。
據報導,前總統馬英九懷念母親最後的病中生活。在母親病榻前念媽媽曾教導過的「桃花源記」等古文作品,因此他支持國文教育裡要多教文言文,多讀點中華文化教材。馬總統記得的這些作品都是清末民初私塾教育的產物,透過教育,階級再製成為某種文化傳遞給總統,總統使用他掌控國家機器的權力,將這個變成人民的意識型態,鞏固特定階級的文化意識。而文白之爭,不過是表象的表象而已。
參考資料:本文參考簡宏逸博士提供的兩篇文章:〈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國語國文論戰〉(未刊稿)、〈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的國語運動與意識型態〉(未刊稿)。